作为阿富汗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喀布尔(Kabul)不会让外来游客失望。黄沙漫天盖不住皇宫的金碧辉煌;破陋的街头、乞讨的儿童与四处可见拿着单反相机的外国游客相映成趣。塔利班的统治已经是昨日故事,但是人们仍然受到宗教法规的严格制约。女性在这个社会里仍然受到包括石刑在内的危害与歧视。9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东宫剧院上演的《喀布尔安魂曲》,讲述的便是那个遥远的文明故都,日夜再现着的人性遗憾。
《安魂曲》难安女性之魂
“喀布尔在哪儿?”以此作为一篇文章的开篇,或许不是件明智的事。保罗·科埃略在《韦罗尼卡决定去死》中,便是以“斯罗文尼亚在哪儿”开篇——斯罗文尼亚女孩韦罗尼卡在一本电脑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以戏谑的语气谈及斯罗文尼亚,视其为世界与文明的尽头;为此,韦罗尼卡决定自杀,并向杂志社写去一封抗议信,抗议人们对于自己家乡的漠视与嘲笑。
喀布尔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可不容小觑。它是一座有3000多年历史的名城,在信德语中是“贸易中枢”的意思。在古代,喀布尔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印度古经典《吠陀经》和《波斯古经》提到一个叫库拔的地方,梵文研究者认为就是今天的喀布尔。中国《汉书》也曾记载过一个叫高附的地方,据考就是喀布尔。古代马其顿亚历山大皇帝和公元18世纪波斯阿夫沙尔王朝帝王纳迪尔沙赫均把这里作为穿越兴都库什山脉南下征服印度的军事要道。公元16世纪初,来自中亚的莫卧儿王朝创建者巴卑尔占领喀布尔。1773年杜兰尼王朝统一阿富汗后定都于此。
这里,古老的皇宫一度美仑雄伟,如古尔罕纳宫、迪尔库沙宫、萨达拉特宫、达尔阿曼宫、巴格巴拉宫、蔷薇宫等。城南山麓的一座伊斯兰圆顶式建筑物“扎赫祠”,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的衣冠冢。城区的东方市场中心有一座梅旺德塔,是为纪念阿富汗的爱国女英雄而建——1880年在英国和阿富汗之间的梅旺德之战中,阿富汗姑娘玛拉莱挺身而出,号召全村男子保家卫国,与阿富汗军合击敌人,终于取得辉煌胜利。玛拉莱的英雄事迹传诵一时,她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女性。
然而,假如玛拉莱活在今天,大概会遭遇有如《喀布尔安魂曲》中姐妹两人的悲剧命运。本剧改编自雅斯米那·哈德纳(Yasmina Khadra)的小说《喀布尔的燕子》。故事的开篇,是低沉的男声宣读塔利班关于社会风气的各项法条:禁止观看电影、写作绘画;禁止播放音乐;男性不许剃须,否则拘留管教;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面纱,不得裸露任何身体部位;禁止涂指甲油,哪只手指涂了指甲油,就砍掉哪一只手指。剧中的一对姐妹,身处于决然不同的状态:姐姐穆莎拉特(Musarrat)恶疾缠身,与从事狱卒工作的丈夫阿提克(Atiq)关系极僵;后者因战争导致跛足,每天面对与自己一样无辜悲惨的生命,无力治疗妻子的不治之症,反而动辄挥杖打骂;妹妹茱莱娜(Zunaira)与丈夫莫辛(Mosheen)在塔利班严格的宗教法规下,都已失业许久。莫辛的外交官梦想日益渺茫,生活日趋拮据,但还算感情深厚,相依为生。
然而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莫辛路过一场正在进行的石刑,他向受刑的女人扔了石头。对此,他陷入了忏悔之中,回家后向妻子茱莱娜述说自己的困惑——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了众人的裹挟与蛊惑,向一个陌生的女人施暴。用《喀布尔的燕子》的作者哈德那的话说:“让弱者向更弱的人施暴,是一种生活极端恶劣情况下的发泄途径。邪恶的制度,会不由分说地将所有人都变成罪人。”石刑就是这样一种刑罚,路过行刑现场的伊斯兰教徒,如果不参与扔石头的行为,就会被视为同情罪犯,甚至与被执行石刑的女犯有染。根据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已婚者犯通奸,只要有四位证人,可以判处乱石砸死。通常把男性腰以下部位、女性胸以下部位埋入沙土中,施刑者向受刑者反复扔石块。如果是对已婚有孩子的妇女行刑,她的孩子必须到现场观看。行刑用的石块经专门挑选,以保证让受刑者痛苦地死去。后来,不只是通奸罪,对于律法记载的其他死刑罪行,也都按例以石刑处理。
进入现代以来,石刑引来越来越多的批评意见。一些人权机构表示,包括石刑在内的伊斯兰司法制度,对于女性存在很大的歧视与偏见。这使得女性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在阿富汗,女性文盲要多于男性,因此一些女性在不识字的情况下可能会招认没有犯下的罪行。在定罪量刑中,女性的弱势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以通奸罪为例,四个男性证人的证词便可以罪名成立;但是女性证人的证词只有在男性证人不够时才可采信,而且一个女性证人只能抵半个男性证人使用。2007年一名17岁伊拉克少女被族人用石块砸死。这段过程被拍成录像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引发人们对石刑的愤怒。录像显示少女被一群咆哮的男子从屋内拖出,随即被当街拳打脚踢,数秒钟之后,她已像胎儿一样蜷缩在地上,用胳膊护住脑袋,努力抵挡着雨点般的石块。一块水泥砸了她的后脑勺,这致命的一击让她顿时血流成河,很快就一动不动。踢打和石砸仍在继续,接着就是男子们得胜的欢呼。
对宗教狂热的反思
据说,本剧的创作灵感起源于一幅著名的摄影作品。1999年11月,一个穿戴着蓝色面纱的女人,在喀布尔的一个体育场被公开处决。她的背影令人困惑而绝望。在《喀布尔的燕子》中,作者哈德纳以此画为背景,讲述了两对夫妇的悲剧命运。原本希望成为外交官的莫辛,在塔利班治下失业挣扎。阿提克作为死刑犯的看守,被黑暗与仇恨玷染了灵魂。两人对于妻子的态度虽然有些相异,但在愤怒或失控时无不会拿妻子泄愤。当莫辛参加完石刑回到家后,对妻子叙说自己的困惑时,妻子没有安慰他,而是显露出恐惧和厌恶的表情——这激怒了莫辛,他对她举拳相向。
争吵中,莫辛不慎滑倒意外死亡。茱莱那则被控谋杀,即将处以死刑。于是她被关入姐夫阿提克看守的死刑监狱。姐姐穆莎拉特四处求助,但是无论是自己的丈夫还是其他的官员,都无情地拒绝帮助。在绝望之中,她决定披着同样的蓝色面纱,以自己的病体替妹妹受死。震撼人心的情节与心理,在《喀布尔安魂曲》的创作团队手中,却以极简的方式表现出来。两个家庭在舞台上仅以两张帷幔加以区别,在幕与幕之间简单切换,种种冲突无奈悲凉凄惨尽现。全剧没有一处闲笔,步步紧逼,然后在高潮处戛然而止,陷入一片漆黑。
对于此剧,著名的观察家菲切尔曾经在《戏剧观察》上作出盛赞:“清醒与疯狂相交织的悲剧。获奖无数的阿默克剧团再次呈现了一部惊世之作,它卓而不群,同时又延续了该剧团一直关注的人性主题。”这是来自巴西的阿默克剧团(Amok Teatro)“战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其它两部分别是《龙》和《家庭故事》。三部曲分别呈现了独立的故事,内在却有着相似的精神——以遥远世界的场景,与当下的生活对话,让观众看到暴力背后的残酷和痛苦,以及那些真正永恒的人类情感。
这部《喀布尔安魂曲》的主旨正在于此。原著《喀布尔的燕子》的作者哈德纳曾经是一位阿尔及利亚军官。原名Moulessehoul的他为了逃避军队文字审查,用了妻子的姓氏发表了多部抨击塔利班非人统治的小说。2000年,他以少校军衔从阿尔及利亚军队退伍,移民到法国巴黎。他的文字被评论家称为“字字滴血,揭示中东战火下的残酷与痛苦,以及那些永恒的人类情感”。这部《喀布尔的燕子》2006年在爱尔兰获得“都柏林文学奖”。他在2006年接受德国广播SWR1频道采访时说:“你们西方人发展了一系列描述世界的方式,并形成了许多理论。但是,这些方式从表面上能够与世界相符,在内在却未必如此。作为一名穆斯林,我也观察着阿富汗发生的宗教狂热。这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我称其宗教同情(religiopathy)。”
哈德纳曾经向读者表达自己的希望:“如果我的小说《喀布尔的燕子》能够给那些平时只能触及我们文化表面的西方观众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触及问题的内核,那就好了。因为,宗教狂热是一种对于所有人都致命的危害。我希望能够揭示它形成的原因与背景,让人们更真实地了解它。或许这样,我们能找到控制它的办法。”或许正是带着这种思考,阿默克剧团将小说搬上舞台,并向全世界展现经历20多年战争创伤的苦难阿富汗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主人公即使长期面对严酷暴力和非人教规,仍然保有的最质朴的人性和尊严。
顺便一提的是,由来自巴西的阿默克剧团上演此剧,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巴西是世界上反对石刑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2010年7月,当时的巴西总统卢拉公开向伊朗求情,希望赦免一位妇女的石刑,卢拉说:“我呼吁伊朗领导人内贾德允许巴西为这名妇女提供庇护。如果我和伊朗总统之间的友谊和我对他的尊敬还值点钱的话,如果这位妇女引起了世人的不适,那么我们愿意接收她。”遗憾的是,卢拉诚恳的请求,似乎没有换来伊朗的热诚。8月3日,伊朗外交部以“卢拉本人并不了解案情”为由,回绝了卢拉的请求。或许,艺术的力量将能够超越政治;这出《喀布尔安魂曲》,或许能够引发人们对于宗教狂热的反思与警惕。巴西、阿富汗和中国相距千万里,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却能够彼此沟通——或许这亦是安魂曲得以抚恤伤痛的原因所在。
Silentnoy_林海 http://read.douban.com/author/63697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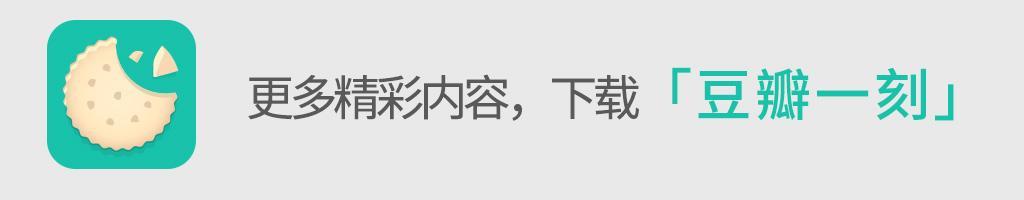
","
发表评论